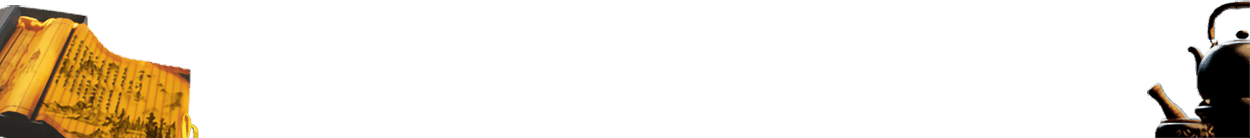|
【美文】余秋雨新作《品鑒普洱茶》二
|
| 發佈日期::2014/3/13、瀏覽次數:3698 |
|
余秋雨新作《品鑒普洱茶》二 普洱茶在陳釅、透潤的基調下變幻無窮,而且,每種重要的變換都會進入茶客的感覺記憶,慢慢聚集成一個安靜的“心理倉貯”。 很多人初喝普洱茶,總有一點障礙。 障礙來自對比。最強大的對比者,是綠茶。 一杯上好的綠茶,能把漫山遍野的浩蕩清香,遞送到唇齒之間。茶葉仍然保持著綠色,挺拔舒展地在開水中浮沉悠遊,看著就已經滿眼舒服。湊嘴喝上一口,有一點草本的微澀,更多的卻是一種只屬於今年春天的芬芳,新鮮得可以讓你聽到山嶴白雲間燕雀的鳴叫。 我的家鄉出產上品的龍井,馬蘭的家鄉出產更好的猴魁,因此我們深知綠茶的魔力。後來喝到烏龍茶裡的“鐵觀音”和巖茶“大紅袍”,就覺得綠茶雖好,卻顯得過於輕盈,剛咂出味來便淡然遠去,很快連影兒也找不到了。烏龍茶就深厚得多,雖然沒有綠茶的鮮活清芬,卻把香氣藏在裡邊,讓喝的人年歲陡長。相比之下,“鐵觀音”濃鬱清奇,“大紅袍”飽滿沉著,我們更喜歡後者。與它們生長得不遠的紅茶“金駿眉”,也展現出一種很高的格調,平日喝得不少。 正這麼品評著呢,猛然遇到了普洱茶。一看樣子就不對,一團黑乎乎的“粗枝大葉”,橫七豎八地壓成了一個餅型,放到鼻子底下聞一聞,也沒有明顯的清香。扣下來一撮泡在開水裡,有淺棕色漾出,喝一口,卻有一種陳舊的味道。人們對食物,已經習慣於挑選新鮮,因此對陳舊的味道往往會產生一種本能的防範。更何況,市面上確實有一些製作低劣、存放不良的普洱茶帶著近似“黴鍋蓋”的氣息,讓試圖深入的茶客扭身而走。 但是,扭身而走的茶客又停步猶豫了,因為他們知道,世間有不少熱愛普洱茶的人,生活品質很高。難道,他們都在盲目地熱愛“黴鍋蓋”?而且,這些人各有自己的專業成就,不存在“炒作”和“忽悠”普洱茶的動機。於是,扭身而走的茶客開始懷疑自己,重新回頭,試著找一些懂行的人,跟著喝一些正經的普洱茶。 這一回頭,性命交關。如果他們還具備著拓展自身飲食習慣的生理彈性,如果他們還保留著發現至高口舌感覺的生命驚喜,那麼,事態就會變得比較嚴重。這些一度猶豫的茶客很快就喝上了,再也放不下。 這是怎麼回事? 首先,是功效。 幾乎所有的茶客都有這樣的經驗:幾杯上等的普洱茶入口,口感還說不明白呢,後背脊已經微微出汗了。隨即腹中蠕動,胸間通暢,舌下生津。我在上文曾以“輕盈”二字來形容綠茶,而對普洱茶而言,則以自己不輕盈的外貌,換得了茶客身體的“輕盈”。 這可了不得。想當年,清代帝王們跨下馬背過起宮廷生活,最大的負擔便是越來越肥碩的身體。因此,當他們不經意地一喝普洱茶,便欣喜莫名。雍正時期普洱茶已經有不少數量進貢朝廷,乾隆皇帝喝了這種讓自己輕鬆的棕色莖葉,就到《茶經》中查找,沒查明白,便嘲笑陸羽也“拙”了。據說他為此還寫了詩:“點成一碗金莖露,品泉陸羽應慚拙”。他的詩向來寫得不好,我當然不會去考證,但如果真用“金莖露”來指稱普洱茶,還算說得過去。 《紅樓夢》裡倒是確實寫到,哪天什麼人吃多了,就有人勸“該燜些普洱茶喝”。宮廷回憶錄裡也提到:“敬茶的先敬上一盞普洱茶,因為它又暖又能解油膩。”由京城想到茶馬古道,那一條條從普洱府出發的長路,大多通向肉食很多、蔬菜很少的高寒地區。那裡本該發生較多消化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疾病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人們終於從馬幫馱送的茶餅、茶磚上找到了原因:“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 當今中國,食物充裕,越來越多的人遇到了清王室和高原山民同樣的問題。因此,普洱茶風行,理由充分。 其次,是口味。 如果普洱茶的好處僅僅是讓身體輕盈健康,那它也就成了保健藥物了。但它最吸引茶客的地方,還是口感。要寫普洱茶的口感很難,一般所說的樟香、蘭香、荷香等等,只是一種比擬,而且是借著嗅覺來比擬味覺。 世上那幾種最基本的味覺類型,與普洱茶都對不上,即使在茶的天地裡,那一些比較穩定的味覺公認,如綠茶、烏龍茶、紅茶、花茶系列所體現出來的味道,與普洱茶也不對路。總之,與這一些類型化、準類型化的味覺定型相比,普洱茶顯得曖昧、含糊、內斂,因此也難以言表。 人是被嚴重“類型化”了的動物,離開了類型就不知如何來安頓自己的感覺了。經常看到一些文人以“好茶至淡”“真茶無味”等句子來描寫普洱茶,其實是把感覺的失落當作了哲理,有點誤人。不管怎麼說,普洱茶絕非“至淡”“無味”,它是有“大味”的。如果一定要用中國文字來表述,比較合適的是兩個詞:陳釅、透潤。 普洱茶在陳釅、透潤的基調下變幻無窮,而且,每種重要的變換都會進入茶客的感覺記憶,慢慢聚集成一個安靜的“心理倉貯”。 在這個“心理倉貯”中,普洱茶的各種口味都獲得了安排,但仍然不能準確描述,只能用比喻和聯想予以定位。我曾做過一個文學性的實驗,看看能用什麼樣的比喻和聯想,把自己心中不同普洱茶的口味勉強道出。 於是有了: 這一種,是秋天落葉被太陽曬了半個月之後躺在香茅叢邊的乾爽呼吸,而一陣輕風又從土牆邊的果園吹來; 那一種,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當歸、二分冬棗用文火熬了三個時辰後在一箭之遙處聞到的藥香。聞到的人,正在磐鈸聲中輕輕誦經; 這一種,是寒山小屋被爐火連續燻烤了好幾個冬季後木窗木壁散發出來的鬆香氣息。木壁上掛著弓箭馬鞍,充滿著草野霸氣; 那一種,不是氣息了,是一位慈目老者的純淨笑容和難懂語言,雖然不知意思卻讓你身心安頓,濾淨塵囂,不再漂泊; 這一種,是兩位素顏淑女靜靜地打開了一座整潔的檀木廳堂,而廊外的燦爛銀杏正開始由黃變褐; …… 這些比喻和聯想是那樣的“無厘頭”,但只要遇到近似的信號,便能立即被檢索出來,完成對接。 普洱茶的“心理倉貯”一旦建立,就容不得同一領域的低劣產品了。這對人生實在有一點麻煩,例如我這麼一個豁達大度的人,外出各地幾乎可以接受任何飲料,卻已經不能隨意接受普洱茶。因為“心理倉貯”產生了敏銳的警覺,錯喝一口,就像對不起整個潛在系統,全身心都會抱怨。 這種拒絕,說大一點,是在人品結構邊緣衍伸了一個小小的“茶品”結構,在人格形態外沿拖拽出了一個小小的“茶格”形態。不管是“品”是“格”,都是通過否定和刪削,來求得等級自守。這對茶事來說,雖然無關精神道德,卻是有涉生活素質。 第三,是深度。 與人們對其他美好飲食的記憶不同,普洱茶的“心理倉貯”,空間幽深、曲巷繁密、風味精微。這就有了徜徉、探尋的餘地,有了千言萬語的物件,有了玩得下去的可能。相比之下,只有法國的紅酒,才有類似的情形。 你看,在最大分類上,普洱茶有“號級茶”“印級茶”“七子餅”等等代際區分,有老茶、熟茶、生茶等等製作貯存區分,有大葉種、古樹茶、臺地茶等等原料區分,又有易武山、景邁山、南糯山等等產地區分。其中,即使僅僅取出“號級茶”來,裡邊又隱藏著一大批茶號和品牌。哪怕是同一個茶號裡的同一種品牌,也還包含著很多重大差別,誰也無法一言道盡。 在我的交往中,最早篳路藍縷地試著用文字寫出這些區別的,是臺灣的鄧時海先生;最早拿出真實茶品在一次次深夜沖泡中讓我們從感性上懂得什麼是頂級普洱老茶的,是菲律賓的何作如先生;最早以自己幾十年的普洱茶貿易經驗傳授各種分辨訣竅的,是香港的白水清先生。我與他們,一起不知道喝過了多少茶。年年月月茶桌邊的輕聲品評,讓大家一次次感歎杯壺間的天地實在是無比深遠。 其實,連沖泡也大有文章。有一次在上海張奇明先生的大可堂,被我戲稱為“北方第一泡”的唐山王家平先生、“南方第一泡”的中山蘇榮新先生和其他幾位傑出茶藝師一起泡著同一款茶,一盅盅端到另一個房間,我一喝便知是誰泡的。茶量、水量、速度、熱度、節奏組成了一種韻律,上口便知其人。 這麼複雜的差別與一個個朋友的生命形態連在一起了,那個天地就有了一種讓人捨不得離開的人文深度。 以上這三個方面,大體概括了普洱茶那麼吸引人的原因。但是,要真正說清楚普洱茶,不能僅僅停留在感覺範疇。普洱茶的“核心機密”,應該在人們的感覺之外。 |